南焱他的名字叫幸福丨天涯散文-“普通人在尘世”小辑
天际微旌旗灯号 :tyzz1996
天有际,思无涯。
点击封面,顿时下单本期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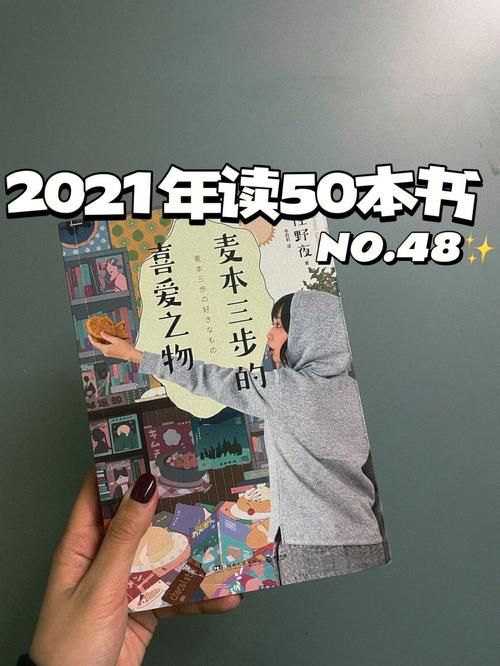
BUY ▷
编者
前言
《天际》2024年第3期的“散文”栏目推出“通俗人在红尘”小辑,陈年喜、南焱、王善常和刘先国以质朴之笔写红尘百态,面临漫漫人活门上的生老病死、爱恨情仇、魔难救赎,通俗人唯有互相寄托、互相支持。
本日,我们全文推送南焱的《他的名字叫幸福》,读者可以在作者的笔墨中,窥见幸福叔“被凌辱和被侵害”的一生。
刘小东《界河》 2019|油彩/画布|250 x 300 cm
他的名字叫幸福
南焱
我犯了一小我所能犯的最年夜的差错,
我没可以或许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博尔赫斯
幸福,年夜约世上大家渴仰拥有。以幸福做名字的人,年夜约世上也不少。我就熟悉一个名字叫幸福的汉子。他是我在湖南老家的近邻邻人,比我年夜一辈,我叫他幸福叔。
昨天晚上,我给母亲打了一个德律风,问及她近日身材状态,她照样时常头晕头痛,胃口也欠好。母亲溘然提及家门前的柚子树,有的柚子已经甜熟了,但前天夜里被人偷摘了几个,埋怨说都是夜里守灵打牌的人摘的(按现今乡里习俗,逝者停灵时代,晚上需雇人守灵,守灵的几人在棺柩旁摆一张牌桌,靠打牌熬彻夜)。给谁守灵呢。我有点诧异。母亲答复说,邻人幸福叔从自家三楼屋顶上摔了下来,先砸到二楼的护栏,再栽落在门前水泥地上,等邻人闻声赶来,他已经没气了。“年夜概是不留心吧,他脑子也不太清醒。”母亲这般说道。
幸福叔是前天照样年夜前天失事的,我没有向母亲求证,这并不紧张,一点也不紧张。只是他死了这个事实仍旧令我有些受惊,究竟他才六十明年。幸福叔曾经是一个爱谈笑的脾气豁达之人,后来则仿若酿成了一块燃尽、冰凉的柴炭,再无半点温热,终而酿成了一个世人嫌弃的“疯子”,现在猝然而逝,更像是一种难以挣脱的宿命。
时针拨回到近四十年前,上世纪八十年月中期。幸福叔照样一个二十多岁的阳光小伙,经常未启齿就咧嘴先笑,样子老实、憨实,有一把子力量,干活不吝力。由于还未婚娶,他和老长者母住在一路。他的哥哥早已成家,有两个儿子,年夜儿子庆瓜跟我年龄相仿,险些每天串门在一路玩。
庆瓜的爷爷奶奶有一个心愿,那便是尽快给小儿子找媳妇。在屯子,幸福叔的岁数不算小了,偏偏多次相亲均不胜利。家里前提欠好,但也不算穷。要是盖上二层红砖楼房,娶媳妇确定不成问题了。那时,一个村落里也就一两户人家盖了红砖房,绝年夜多半是住土砖瓦房。盖红砖房不容易,家里蓄积不够,显然是不行的。幸福叔家是土砖房,要盖新居,还得费力攒上几年钱。
屡屡相亲不成,一家人很是郁闷。庆瓜爷爷性格急躁,日常平凡爱躺在屋檐下的一张破竹椅里,用裁碎的纸条,包上本身种的烟叶丝,卷成喇叭筒,整齐根火柴点燃,年夜口年夜口抽旱烟,喷出的烟雾异常呛人。一天,他一边嘴喷浓烟,一边冲着幸福叔扬声恶骂,而幸福叔也一改温驯性格,把老头目连人带躺椅,一把推动了门前的臭池塘。庆瓜爷爷在臭池塘里扑腾,比落汤鸡更狼狈,挣扎着爬上来接着扬声恶骂。庆瓜奶奶一边给老头目洗脏衣,一边直抹满脸老泪。
没能盖新居,可以想其他门路啊。1985年的秋日,一天下学后,我刚回抵家里。庆瓜就促跑来找我,说叔叔家买了一台电视机。那时,村落里还没人有电视机,一据说幸福叔买了电视机,纷繁过来瞧个新颖稀奇了。
那是一台火赤色外壳、14英寸的诟谇电视机。幸福叔动作和顺,像抱一个婴孩般,把它从纸箱里当心翼翼抱出来,轻轻放在柜子上,转弄着天线调收频道。我们这帮小孩,看得心神专注。当布满雪花点的荧屏呈现画面时,房子里的人全都欢呼起来。那天为了多看一下子电视,我坚决不吃晚饭,对妈妈重复催我回家的喊声视而不见。
买这台电视机年夜约花了五百元,当时对田舍来说消费不菲。庆瓜奶奶咬了咬牙,把栏里的一头肥猪卖了,还卖了几百斤谷子,加上女儿给的一些钱,总算把电视机抱回来了。幸福叔感到还不够齐全,又四处借钱去买了一台灌音机。
当时,年夜部门村落平易近家里,最高真个“电器”不外是手电筒。幸福叔家同时拥有电视机、灌音机,派头立刻上去了。过年的时刻,他从城里带回几盘磁带,往灌音机里啪的一插,摁下开关按钮,音量调到最高,欢快的歌声在空气里涟漪,四邻都听得清清晰楚。幸福叔最爱听的一首歌是邓丽君的《回外家》:“风吹着杨柳哗啦啦啦啦啦,小河里流水哗啦啦啦啦啦,谁家的媳妇儿,她走得忙又忙呀,本来她要回外家……”许多年以后,这首歌的旋律依然在我的脑海里回荡。
说媒的人也多了,庆瓜奶奶昔日一脸的愁苦,也绽出笑脸了。然而,每次相亲后,不是人家姑娘不满足,便是幸福叔不满足,一年多下来,竟然照样没有定下工具。庆瓜奶奶又规复了一脸愁苦。庆瓜爷爷又经常一边抽着纸喇叭烟,一边扬声恶骂。幸福叔的反响也没以前那么剧烈了,也就张口结舌。
但幸福叔照样每晚把电视机抱出来,摆到表面宽敞的晒谷场上,便利邻里年夜伙儿看。只要不绝电,每晚园地里都要围满老小几十号人,没带凳子的小孩乃至爬上树,坐到树杈上看电视。电视剧《霍元甲》《陈真》《上海滩》等,便是我们心中的最爱,也是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有一次,我在家练羊毫字,一时髦起,提笔蘸墨来到幸福叔家,在门中间写上《霍元甲》主题曲中的“万里长城永不倒”几个斗年夜的黑字。字写得歪七扭八,墨汁却渗进了木头,像一排秃毛乌鸦般丑恶。幸福叔用抹布蘸水,怎么擦也擦不失落。但他也只是笑笑罢了,对我并未有任何责备。
在这个时期,村落里的宁靖叔溘然查出得了喉癌。癌症很可骇,年夜伙儿都这么传着。宁靖叔住在年夜屋院子,那边有几排凹字形的家传瓦房,好几户人家拥挤着住在一块。我们这帮小孩,常去院子里玩。每户人家平凡也不关门,我们就在各间老房子里穿梭,玩捉迷藏的游戏。
宁靖叔已婚,跟媳妇文英情感很好,有一个两岁的儿子小武。当初,在宁靖叔新婚之后,我们这帮小孩还去他家窗下窃视。他和媳妇有时躲在蚊帐里亲切,一发现我们躲在窗下,就跳下床来撵我们。他为人和蔼,从不骂脏口,日常平凡爱鼓捣钟表。文英婶身体饱满,不算漂亮,但也眉眼含春,待人也热心。圆满的三口之家,却因癌症蒙上了阴霾。文英婶每天熬药,而宁靖叔都进不了食了。
没过多久,宁靖叔就死了。逝世的那一天,他坐在椅子上,骨瘦如柴,低垂着头,面色苍白如纸,如木偶般被抬到停棺材的堂屋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死人的样子容貌,却一点也不畏惧,只是感到样子有点怪僻。文英婶哭得死而复活,把额角都磕出血来了。宁靖叔下葬后,剩下文英和小武这对孤儿寡母,以后日子欠好过呀,左邻右舍这么看在眼里。
一个月后,经村落里的老太太热情撮合,文英婶批准再醮给幸福叔。没过多久,她还带着小武搬进了幸福叔的家里。庆瓜奶奶甭提多愉快了,成天地头、灶头忙着,不让文英婶干一点家务活。幸福叔也是满面东风,便还没过年,就把灌音机拿出来放音乐。《回外家》的欢快歌声,在房子的每个角落里回荡:“……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背个胖娃娃……”统统尽在不言中,也就剩下领证办酒的事儿了。
大概是冬天夜里冷,白叟受不了凉,庆瓜爷爷病倒了,在床上躺了几天,竟然逝世了。喜事还没办,凶事得先办了,令人沮丧。老头目习气每天嚷嚷,嘴里含着喇叭筒旱烟,不那么招人喜欢,但一旦没了他,四周宛如一会儿冷清了很多。幸福叔和一家人披麻戴孝,未嫁过来的文英婶也穿了孝衣,家里氛围也不生动了。电视照样放给全村落人看,但灌音机已经静静收起来了。
庆瓜爷爷才入土为安,村落里又失事了。宁靖叔有一个胞兄,日常平凡在铁路上事情,一直没有婚娶成家。听闻弟弟逝世,他赶回来后,精力受到刺激,从此有点不正常。也不去上班了,经常一小我在老房子里发呆,偶然出来逛逛,也显得精力恍惚。有一次,他纵火把邻人的一间茅房点着了,固然被实时毁灭,没有闹出年夜事,但村落里人都说他疯了。
在庆瓜爷爷逝世后不久,一世界午,我们又去年夜屋院子玩捉迷藏。在宁靖叔家里陡然发现他的兄长像一只瘦鸡一样悬在房梁上,双腿一动不动,眸子子鼓凸,舌头伸得老长。黑魆魆的老房子里,光芒惨淡,透着一股阴沉森的气味。那一天,我第一次觉得殒命的可怖,吓得晚上睡觉蒙在被子里,年夜气不敢出一声,连外出上茅厕都不敢一小我去。之后,我再也不去宁靖叔家玩了,总觉得那边彷佛有一双莫名的眼睛在暗中中盯着我。
宁靖叔还有一个已出嫁的妹妹,凶事就由她来筹划了。文英婶带着小武,也去尽份内之事,又是披麻戴孝。按乡里习俗,寻短见的过于不利,凶事办得潦草,没有办酒菜,来客也无多抚慰,乐手们勉强吹奏乐打一番,几名壮汉把棺材促抬到山上,挖一个坑埋失落完事。
此时,村落里的飞短流长已经起来了。有爱嚼舌头的妇女暗里传说:文英婶是一个年夜扫帚星,是一个狐狸精,先是克死了丈夫,来到幸福叔家里又克死了老头目,还接着克死了丈夫的哥哥。如许的女人,谁娶进家里谁倒霉。又有爱嚼舌头的汉子暗里传说:这个女人命太硬,幸福对她言听计从,怕是制不住她,还没娶亲就闹成如许,以后难说了。
过年开春之后,幸福叔预备领证、办酒菜,光明正大把文英婶娶过来。提前两周就置办了一些喜糖、烟酒、鞭炮,新婚用的镜子、浴盆、箱子等也买了回来。年夜伙儿固然心里怀疑,但也等着吃喜酒了,不绝地问,哪一个日子。幸福叔笑着答,就快了。庆瓜奶奶仍旧忙前忙后,照样满心欢喜。
选了一个黄道谷旦,两人换上新买的衣裳,一年夜早前去乡当局去挂号了。快到的时刻,文英婶突然对幸福叔说,本身想先回外家一趟,奉告她老娘一声,顿时就赶回来。幸福叔要求陪伴前往。但她说不消了,办完喜酒他再去更好,本身最多两三个小时就回来。幸福叔感到有理,就依她言,约好到乡当局后等她,趁便逛了好一下子集市,买了一些酒肉,预备挂号完归去后炒几个佳肴,自家里先庆贺一下。
那一天比及黄昏,也不见文英婶回来。他急了,顾不得那么多,就年夜步直奔文英婶外家。到了后一问,本来她基本没回外家,已经不知所踪。庆瓜奶奶煮好了饭菜,一直没有吃,在等儿媳回来。子夜里,幸福叔回抵家时,阴森着脸,像泄了气的皮球。庆瓜奶奶问才知缘故原由,失声年夜哭起来,把邻人都惊醒了。而小武在近邻房子里,一小我睡得很香很沉,不知道本身已经被妈妈摈弃了。
文英婶无情地摈弃了幸福叔、小武,独自跑到远方某个处所去了。村落里又有人暗里传谣,说幸福叔那方面不太行,不理解睡女人,文英婶对他很不满,是以就跑了。村落里年青人则暗里讥笑幸福叔是个软蛋,一辈子都硬不起来。
许多年内,文英婶泥牛入海。后来听人说她嫁给了一个铁路工人,但从没回来看一下儿子。小武八九岁的时刻,每当别人提起她妈,他就狠狠地说,她早就死了。
幸福叔没能结成婚,喜酒天然也黄了。宁靖叔的妹妹,也便是小武的姑姑,把小武接到她家去了。幸福叔家里马上冷清下来,母子俩好生凄凉。那以后,庆瓜奶奶变得加倍苍老了,像一块焦黑的炭,表情再无光荣。
喜糖放在柜子里,对小孩很有吸引力。趁奶奶、叔叔在地里干活,庆瓜时常偷偷翻开柜子,一次次把喜糖拿出来,与我们这些小玩伴分吃。不到一个月,喜糖便被我们全体偷吃光了。
当我们把末了一颗糖塞进嘴里,觉得百无聊赖时,庆瓜从家里的床底下发现一壁铜锣,于是扒了出来,当当本地敲起了锣。锣声把奶奶引来了,只见她表情丢脸,伸手抢走了锣,责备了庆瓜几句,要他别再敲了。
据老家的习俗,家里如有人逝世,家眷便敲着铜锣去江里打水,回来给死者净身。庆瓜敲得起劲的铜锣,恰是此前他爷爷逝世时用过的。这锣声天然不吉利,像是一句谶言,让他奶奶觉得心惊胆颤。
一天早上,幸福叔去山上砍了一棵枫树,跟庆瓜奶奶一路抬了回来。这棵树不年夜不小,但也挺沉,庆瓜奶奶抬着异常吃力,后背驼得厉害。我家正吃早饭,父亲放下碗筷去替庆瓜奶奶抬树,我也端着饭碗去观看。枫树抬到屋旁旷地,父亲先放下树,前头的幸福叔随后也把树从肩头抛卸到条凳上,孰料这么一抛,那棵树从条凳上弹起来,再落下时正好砸到我的头上,我被砸趴在地,马上头破血流,把所有人都吓坏了,幸福叔、庆瓜奶奶更是伯仲无措。父亲赶紧背上我送去乡病院,对伤口进行了止血处置,幸好没有年夜碍,但我的头上从此留下了一道疤痕。
我头上的伤口年夜概方才病愈,六月的一个薄暮,天色暗了下来,怙恃还在地里干活,没有回来,我煮好了饭,正在门前的桃树下坐着,庆瓜奶奶捧着一袋熟李子送过来,塞进我的手里,说是给我吃的。我收下后,掏出一颗就嚼了起来,李子的果肉微甜而酸涩。她见我吃得欢,木刻般的脸上绽开了笑脸,随后弓着背逐步走归去了。
许多年后,我回忆起来,才感到她其时的笑脸和背影,竟是无以形容的苍老、凄凉。第二天一年夜早,母亲奉告我,庆瓜奶奶头天晚上逝世了。
庆瓜奶奶一小我住在一间老屋里,夜里就喝下年夜半瓶敌敌畏,喝农药后毒发,双手痛苦地敲拍着门。庆瓜妈妈夜里起床小解,听到婆婆屋里的响动,就凌驾去瞧。她还认为是黄鼠狼来叼鸡呢,一看婆婆的样子,吓得赶紧唤醒丈夫、幸福叔和邻人。年夜家跑来看时,庆瓜奶奶躺在地上吐着白沫,已经不行了。
等我跑去看时,庆瓜奶奶已经入了棺。一口未油漆过的薄皮棺木,停放在堂屋里。近邻的房子里还残留着一股刺鼻的农药气息。我觉得很不测,但又什么都说不出来。跟年夜人们严肃的脸色完全纷歧样,我和庆瓜这些孩子,一点也不觉得伤心,宛如感到这挺天然的。乡里流行办白喜事要放片子,看片子的氛围跟过节似的,我们这些孩子都颇是等待。
庆瓜奶奶的墓,跟他爷爷的墓紧挨着。他爷爷的坟头还没有长出多高的茅草,两座坟看上去都是新的。庆瓜奶奶为什么要喝药自杀呢。如今也说不清晰。
老长者母接踵过世,幸福叔彻底成了一个王老五骗子。一小我下地干活,一小我做饭洗衣,煮一锅饭要吃上一天。由于接连办白喜事,花了一些钱,庆瓜妈妈也对幸福叔有牢骚。家中这般霉运光景,天然是没人再登门说媒了。幸福叔垂垂成了四邻村落里著名的王老五骗子。
如斯过了两年,打工潮开端鼓起,村落里年青人也先后找机遇去年夜城市的工场营生了。在亲戚的先容下,幸福叔前去广州一家猪饲料添加剂厂打工,干的是体力活。这比在家种地要强多了,费力干了两年,若干也算攒了一点钱。之后,他又回来预备盖红砖房了。先是雇人打砖、烧砖窑。那窑火烧得旺,待熄灭、冷却后,把窑砖扒出来一看,一窑红砖呈猪肝色,但又未烧过头,可说是可贵的上等好砖。年夜家都笑说幸福叔时来运转,要走红运了。他也整天乐呵呵的,连轴转不安歇,拆失落了老土砖房,盖起了四间红砖平房。
这个时刻,红砖房已经绝不稀奇了,村落里许多人家都盖了新居。电视机更是遍及,年青人还买起了VCD播放器,再也没有人到幸福叔家看电视了,相比之下,他家的电视机从屏幕年夜小到外观设计已周全掉队了。固然他住进了新居,偶然也有人来做媒,但照样没有谈成,并没有呈现好运。跟着年岁渐长,幸福叔娶媳妇的愿望,也变得越来越迷茫,他茕茕孑立,孓然一身。
我上初中后,放寒假回家,想着幸福叔家还有一台灌音机,就跟他借灌音机来放歌。他倒也痛快,把那台寄存已久的灌音机提给了我。其时我哥已经上年夜学,从黉舍带回了《人鬼情未了》《风月俏佳人》之类的外国歌曲磁带,我就用幸福叔的灌音机,听起了这些外国歌,还听香港四年夜天王的流行歌曲。有时一边在厨房土灶边烧火烧饭,一边高音量放歌,烟熏火燎中,《人鬼情未了》蜜意缱绻的歌声飘扬。
幸福叔还去过广州打工,但后来那家添加剂厂倒闭了,他又回家种地了。屯子独身只身汉的生涯一每天反复,彷佛也没有太多可说的。
那时种地费力又不挣钱,屯子钱粮尤其名目繁多,“三提五统”这个本日已经彷佛显得生疏的名词,当时倒是农夫身上结壮实实的重负,压得很多家庭喘不外气来。有一年母亲又生病,我家的经济即时陷入逆境,我那时读高中,新学期的膏火全指望栏里养的一头猪了。那头猪也挺争气,吃糠咽菜,倒是蹭蹭地长,体肥膘厚。暑假时代,恰好几里地外的邻村落有一家人办白喜事,必要买一头猪办酒菜。父亲就请来屠夫把猪宰了,把猪肉分成两担挑去邻村落卖给那家人。
父亲的一条腿有痼疾,幸福叔遂前来协助。他挑了一担猪肉走在前面,我挑了一担跟在后面。每担都重达一百多斤,幸福叔的那担要多重四五十斤。恰逢炎天下暴雨,墟落小道上满是泥。幸福叔戴着笠帽,光脚踩在泥水里,一步一步挪动。我也戴着笠帽,光脚走在后面,步子更是踉踉跄跄。我俩唯恐跌倒在泥地里,宁可被雨淋,也不克不及把猪肉摔坏了。总算挑到邻村落交付完毕,满身都湿透了,雨水、汗水混合,裤管往下直滴水。那幕雨中泥地里艰巨前行的情景,我至今影象犹新。
再过几年,我也上年夜学了,分开了老家。因回家次数稀疏,对老家的人事也垂垂疏远。卒业事情后,照样如斯。偶然返乡,也是促待几天就走,跟幸福叔天然也谈不上有若干交流,乃至基本见不到一壁。这十余年间,他把红砖房又加盖了一层,还里外粉刷了一番,窗户也换成铝合金的,一幢白色的小楼,看起来还不错。他照样一小我过日子,一小我住在那小白楼里。
年夜屋院子的老屋早就无人栖身,在风雨中一间一间逐渐坍毁了,沦为一摊砖瓦废墟,杂草丛生。本来住在这里的人家,也早已陆续搬走了。小武的姑姑一家子,也带上小武去城里捡废品营生计去了,已经多年没回村落里,旧屋子也是无人看守,一每天地颓坏下去。
前些年有一次春节回籍,我偶尔见到了幸福叔。他正挑着水桶去井边担水,他老了很多,形若槁骸,无声无息,影子般的存在。我上去打了一声招呼,递给他一支卷烟,他低声嗯了一下,接过卷烟夹在耳朵上,也不正眼看我,便侧着身子径自挑水去了。我想,年夜概是我们多年未见吧,终究是陌生了。
他天天都缄默寡言,日常平凡年夜多躲缩在家里,不出来跟其他人措辞,包含他的兄嫂一家。年夜岁首年月一,依照习俗,邻人们纷繁互相贺喜贺年,只有他韬匮藏珠。我把过年家里做好的菜,打好了一年夜包,给他送了曩昔。拍门几声,没多久,门开了一条缝,幸福叔站在门后暗影里,没有任何脸色。我跟他阐明来意,把包递曩昔,他依旧是嗯了一声,一只手把包接曩昔,另一只手随后把门关上了。
我感到十分诧异,幸福叔何故酿成如许了。于是向邻人们探听缘故原由,他们说了如许一个简短而感伤的故事。
本来,三年前,幸福叔曾经在县城的一家糖厂打工,跟厂里的一位中年女工相熟。这位女工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一个小男孩,她比幸福叔小十几岁。幸福叔很疼爱这个孩子,常常给他买好吃好玩的器械,还时常帮衬这位单亲妈妈,彼此相处融洽得形统一家子。
在糖厂的同事们看来,他俩日久生情,应该是好上了,娶亲是迎刃而解之事。那一阵子,幸福叔劲头很足,看上去也年青了很多,逢人也是喜逐颜开,回家请人把屋子里里外外装修睦了,完全相符屯子婚房的尺度。
等幸福叔的屋子装修完了,那位单亲妈妈却暗里静静分开了糖厂,带着孩子去广州打工了。幸福叔得悉后,也顿时赶往广州,十分困难找到了她。那位单亲妈妈也还算热心,到宾馆给他开了一间房,请他吃特点美食,陪他在广州嬉戏了几天。之后,她买了一件新衣服和一张返程车票,塞给了幸福叔,委婉回绝了他的求婚。
幸福叔没有纠缠,独自默默踏上了返乡的列车。回来后他像是完全变了一小我,彻底丢失了精气神。他不再跟年夜家谈笑,变得缄默寡言,乃至亲戚邻人跟他打招呼,他也绝不理会。他依旧独自种菜,也去赶集卖器械,偶然会说几句话,但年夜多时刻险些完全哑寂,形统一个影子。逐步的,年夜家也不再搭理他,对他缩手旁观。
因为独身只身无后,依照五保户的养老政策,幸福叔可以去镇上的养老院,村落委会也一片美意,给他办了手续。但他死活不愿去。他开端骂人,骂所有的人,尤其是骂村落里那些发家不明、神气显摆的人,骂得还极其难听。被骂的人装聋作哑,全当没听见。年夜伙儿早已把他当成了疯子,谁会跟一个疯子计较呢。他照样会种菜,也照样挑着菜去县城街上卖。要是有人来买菜,他却报以大骂,骂买菜的人只知吃不知种菜。这么一骂,便没人敢来买了。看到菜卖不出去,他便接着骂,骂众人有眼无珠,骂过路人不买他的菜。
他成了乡里远近驰名的疯子。他的兄嫂也受不了他的毒舌,接受别人的建议,把他送去了精力医院。听说在那边,幸福叔一度被绑缚四肢,穿上了紧身衣,吃了不少苦头。在精力医院待了年夜半年,又被送回到了村落里。见人骂人的习气也有好转,他又酿成了缄默寡言,经常躲在家里,但再也不种菜了。兄嫂天天用饭时,趁便会给他送去一碗饭菜,但也仅此罢了。其他人更是如避瘟神,躲得远远的,不肯意跟他说一句话。
听母亲说,幸福叔后来养成了一个习气,便是天天朝晨起来,来到后山上,四下捡一些枯枝败叶,生起一小堆火,经常被青烟呛得涕泪交流。只要没激发山火,村落里也没人管他,也没人问他生火干什么。
有一点确凿无疑,那一小堆野火,点燃,熄灭,又点燃,却永久也暖和不了二心中层层聚积的严寒。那种严寒到底有多深邃深挚,大概我永久无法懂得。我独一知道的是,他在刻入骨髓的孤单中一每天朽迈,末了在无人存眷的环境下,从楼顶上重重摔落下去,给他辛劳、低微而又无比荒漠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南焱
湖南衡阳人,作家、资深媒体人。卒业于复旦年夜学中文系。在《北京文学》《天际》《山花》《南边文坛》等杂志颁发过多篇小说、诗歌、散文及批驳文章,在《人平易近日报》《北京日报》《文报告请示》《新京报》等着名报刊上颁发过数百篇文化时评、影评、书评及散文漫笔。著有诗集《北极星为谁指路》等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