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风一笑抒情散文父亲
父亲突然老去,揪心的痛成为我的遗憾。不知道。谁人天下是否存在。不知道。他是否孤单抽着旱烟。不知道。他能不克不及收到清明的纸钱。不知道。谁能治疗我的忧伤和想念。
想到父亲,我心存愧疚
爷爷为逃水患,拖家带口分开固始三河乡的圩区,在杨集乡一个村落打谷场安家。由于操劳过度,爷爷刚到新处所就逝世。年夜伯外出讨生涯,二伯成亲分居。奶奶多病,姑姑腿有残疾。十六岁的父亲早早地担起养家重担,从小就形成了吃苦刻苦,坚韧不拔的脾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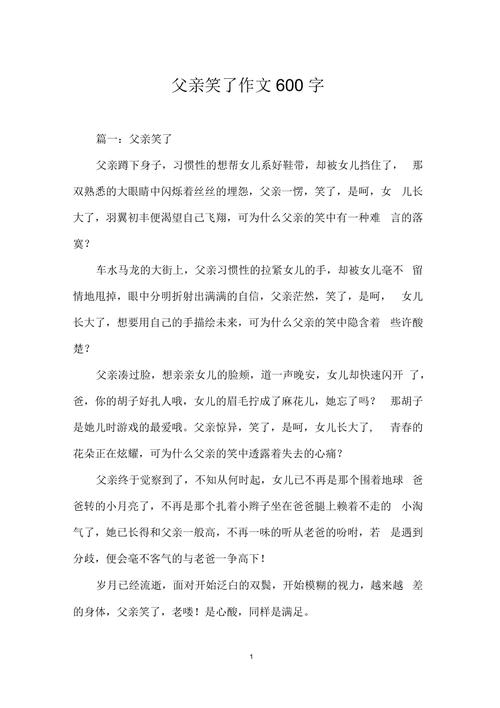
十八岁那年,父亲在别人家的门房里,娶了同样孤儿寡母的母亲。第二年,父亲和母亲用勤劳的双手,垒起一间属于本身的斗室子。他们辛勤劳作,老是拿临盆队最高的工分,日子逐步地变好。我们兄妹五个接踵出身,给他们的生涯增长了许多乐趣,也带来很年夜压力,从记的时刻起,父亲一直在不绝地劳作。
小时刻河塘里鱼多,父亲会抓鱼远近驰名,他能把竹签削得很细,两端尖尖,用丝线栓住,制成卡钩,带有弹性竹签,卡上麦粒做的饵料,栓在细细的尼龙绳上,晚上放的堰塘里,早晨能收的许多的鲫鱼,白条。他还会编织搂网,两个长竹竿挑着,能搂到各色杂鱼。小时刻最喜欢下雨,尤其是炎天的雨后,父亲总能抓到许多鱼,年夜的拿到集市卖,小的就可以犒劳我们。我们兄妹几个都喜欢吃鱼,喜欢鱼的腥味,妈妈老是絮聒,吃鱼多用猪油。日子固然艰巨,童年有许多美妙的回忆。
集体吃年夜锅饭时,父亲由于能把一年夜铁锅饭烧熟,当选为临盆队做饭。刚开端时老是有剩饭,父亲很有远见,可以拿回一点点。奶奶把剩饭晒干,舂成米粉寄存起来。集体食堂停火以后,开端打饥荒,全村落断火断炊,这一点点米粉,加上母亲挖的荸荠,干苜蓿,当夜深人静时刻,用我家独一的瓦盆熬一点点稀稀的苜蓿荸荠汤,让一家人渡过存亡关。
父亲还能赞助人做菜,那时刻会烧菜的人少,父亲脑子机动,表面吃一次红白宴席,就学会本身做。其时常常集体出工差,挖塘修渠,由于会做菜,父亲老是赞助煮饭,也算是比拟安闲的工种。偶然遇到的红白喜事,帮人做菜,不像如今给钱,有时会给一小块肉,或者半块鸡作为礼品,那每每是我们兄妹的节日,能吃一次香馥馥的美食。
村落里一个改行武士办了一个识字班,小时刻我最油滑捣鬼,不知道怎么了,到黉舍却分外地宁静,先生常常在妈妈面前表彰我,妈妈感觉分外有体面,就一直保持让我上学。父亲十分不甘心,愿望我能早早干农活,减轻家里的负担。我们弟兄三人,年夜哥初中卒业回村落劳动,能挣工分,得父亲喜欢,弟弟小,每天随着他甜甜地腻歪着,父亲疼爱,两个妹妹小,最是父亲的疼爱。我由于上学,不克不及帮家里一点点忙,每个礼拜还要从家里拿钱,感觉不喜欢我。小学卒业,我考上了乡里的中学,必要住校,还要交膏火、炊事费。谁人年月,天天几毛钱,也是我家一笔最年夜的开支。每次要钱,看着父亲艰巨的样子,我心里难熬难过,然则又不得不向父亲伸手。
家里原来艰苦,由于我的上学,家里加倍艰苦,父亲常常为我多费钱费心,家里由于我上学加倍艰巨。父亲很少对我笑,不像对年夜哥,更不像对弟弟那样,我从不敢和父亲轻松措辞,更不敢像弟弟那样撒娇,父亲对我始终都是威严的,这种威严一直延续,那时我基本不睬解父亲,对父亲的远远没有对母亲亲近。心坎老是畏惧父亲,然则又十分依附父亲,老是盼望从他那边获得一些赞成,每次获得奖状,取得好的成就,他对我老是轻描淡写,远没有母亲那样愉快,自满。
我上学时刻,没有家庭功课,礼拜日可以赞助干点农活,我老是找托言,看书呀、写字呀、不想干农活,哥哥弟弟都故意见,父亲不让我礼拜天看书,要求我好好干活。记得有个礼拜日,从同窗那边借一本小说,礼拜一必需还给同窗,正遇上家里剥红麻,我心心念念小讨情节,父亲在的时刻,还算老实,父亲有事走了,我什么也掉臂,拿上书,翻过屋后的渠道,躺到田埂上,暖阳下细细观赏我的小说。父亲回来,十分朝气,年夜哥乘隙起诉,拿上赶牛的鞭子,在年夜哥的指引下,趟过屋后的沟渠,瞥见躺在田坎上出神的我,基本来不及反响,腿上已经两道鞭印。这是我第一次挨打,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我十分自责,日常平凡不克不及帮家里一点点忙,礼拜天,家里那么忙,还要搞特殊,毫无忌惮哥弟的感触感染。母亲心疼我,和父亲年夜吵了一架。几个礼拜后,回抵家,母亲拿出一双白色回力球鞋,我求之不得的白色的球鞋。我只是向母亲提了一次,父亲在集上看看了价钱,老是舍不得,此次绝不犹豫的买下,让母亲给我。这大概是父亲歉意,实在我其时只有自责,不克不及为家里分忧,反而给家里增长负担,看到父亲不测的礼品,我知道那是父亲熬若干次夜,辛勤的劳作换来的,我刹时懂得了父亲,突然感觉父亲的威严是那么的可敬。
父亲为了每个礼拜的几块钱炊事费,他要隔三差五熬夜,扛着搂网,忙完所有的活计以后,趁着夜色去很远的处所搂鱼,第二天又早早拿到集市卖钱,还不克不及耽搁第二天的劳动,有时早晨很夙兴床抓到鱼后,匆忙去赶一个早集卖钱。逮鱼摸虾绝对是一项费力受累的活,没有几小我可以或许一直保持下去,由于要起早贪黑,常常和水打交道,常常有危险。父亲就像一个不绝扭转的陀螺,地里田里,犁田耙地,赶集卖鱼,出门做菜,一直都在忙繁忙碌。 就如许,父亲一直费力劳作,历久熬夜,常常和水打交道,也给他的身材埋下了病根。我还老是不睬解父亲的费力,总感觉父亲有无限的力气,无所不克不及。
因为常常赶集,他十分相识市场行情,联产承包以后,农闲时常常在城乡集镇间往返倒腾,赚点差价,这些都是费力钱,便是这点费力钱,保证了我的膏火,艰巨造就一个年夜学生,后来,我事情以后也做点小买卖,赚点小钱贴补家用,可能便是受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卒业以后,有了人为收入,日子好了一点,接着授室生子,父亲并没有享到我的福,反而给他增长麻烦。儿子出身后,没有人领,只能让妈妈过来赞助带孩子,那时屋子小,不克不及让父亲一路过来住,他也舍不得家里的庄稼,五十岁的父亲,恰是必要母亲照料的年龄,没有母亲在身边,一小我孤单的生涯在乡间。
后来前提轻微好一点,把父亲接过来和我们同住,闲不住的父亲老是想干点工作,他最年夜的希望便是有一台本身的灵活三轮车,在街上收废品,或者倒卖一些农产物和生果,卖一些甘蔗,菠萝。然则,我老是托言平安,加上一点点体面问题,一直没能满意他的希望。操劳一辈子的父亲,突然闲下来,不克不及顺应城市的生涯, 总感觉被人轻忽,总想白手起家,不想过早的吃闲饭,愿望我能帮他找一个看门的事情,来赡养本身,不想过早的安闲,分开老亲旧眷,在不认识的城市,父亲老是有莫名的孤单,可是,我从来也不知道和他交流一下,每每不睬解他的苦痛。
十多年前,父亲突然离世,那天早晨,他脑溢血突然昏摔倒在菜市场,没有留下一句话,突然的分开,给我留下永远的痛,每当瞥见和父亲年事相称的白叟,会有莫名哀伤涌向心头,总感觉没有向父亲尽孝道,遗憾一直缭绕着我,父亲的音容相貌,历历在目,思念之情油然而生。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一直探求我的过失,我的遗憾,生涯方才好一点,方才才开端幸福的老年生涯,可是他一声招呼不打,突然分开,我的心坎十分愧疚,跟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愧疚越发强烈,若干次在心中,我一直都在查找,假如给父亲量一量血压,假如可以或许给他反省一次身材,假如不让他日常平凡喝那么多酒,假如.....,假如.....,我心坎想了许多,一直没有谜底.
如今前提好了,对父亲的愧疚日益加深,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刻,在深深的梦魇中,总有对父亲蜜意泛起,这种情感不知道怎么表达。我耳边又缭绕一首小诗:
父亲
犁铧锃亮映着星光
老牛在前
骑在父亲的肩上
父亲驮着我
和着故乡的小调
走过油菜花的清香
童年的影象
扎实便是父亲宽厚的肩膀
蓑衣披在身上
骤雨顺着茅草流淌
当彩虹挂在天涯
生擒到瓦盆里几尾鲫鱼
一壶米酒
我快活的夏日
停顿在泛黄的阴历中
仅仅剩下父亲爽朗的笑声
水稻哈腰的时刻
木锨扬起委顿的腰身
成熟的季节
父亲脸上挂着劳绩的笑
抽一袋旱烟
黄昏下的晒场
秋虫啾啾
坦然便是宁静地躺在你的臂弯
下雪是的季节
眉毛上落下点点白霜
全是皱纹脸上
看不清被寒风吹出了皴裂
艰辛之痛,砭骨之寒
在父亲脚上磨出了操劳的水泡
在血与土的粘合中
被光阴刺破,固结成耐磨的老茧
铮亮的柴刀
在蹭布上中逐步钝去
滑腻的弯镰长出苍老的锈斑
我没有一点预备
父亲突然老去
揪心的痛成为我的遗憾
不知道
谁人天下是否存在
不知道
他是否孤单抽着旱烟
不知道
他能不克不及收到清明的纸钱
不知道
谁能治疗我的忧伤和想念
